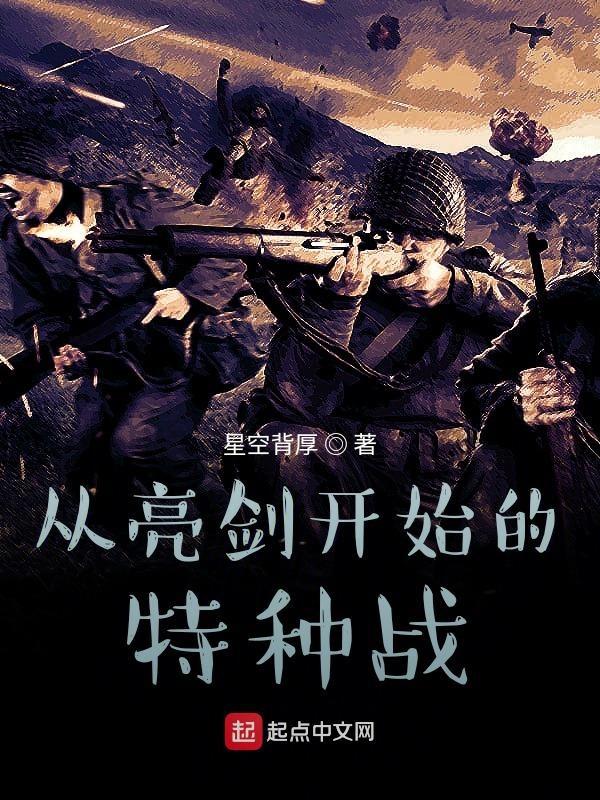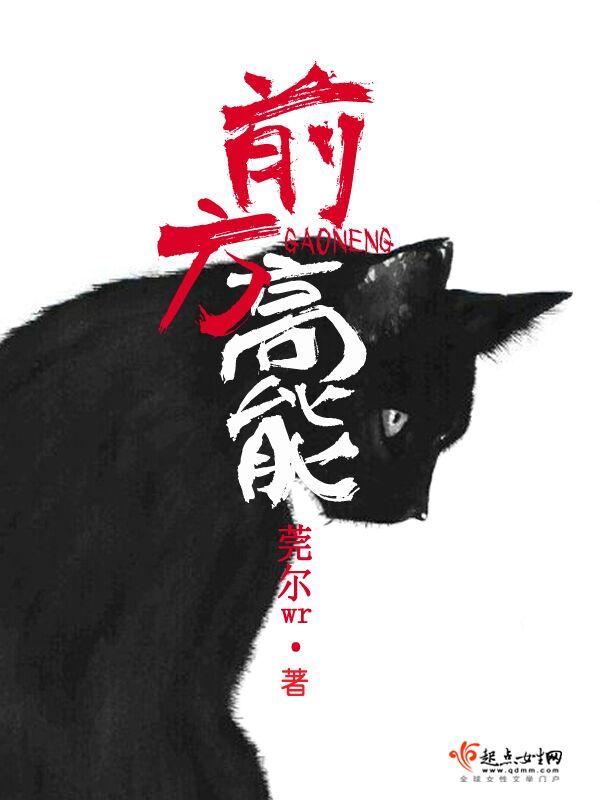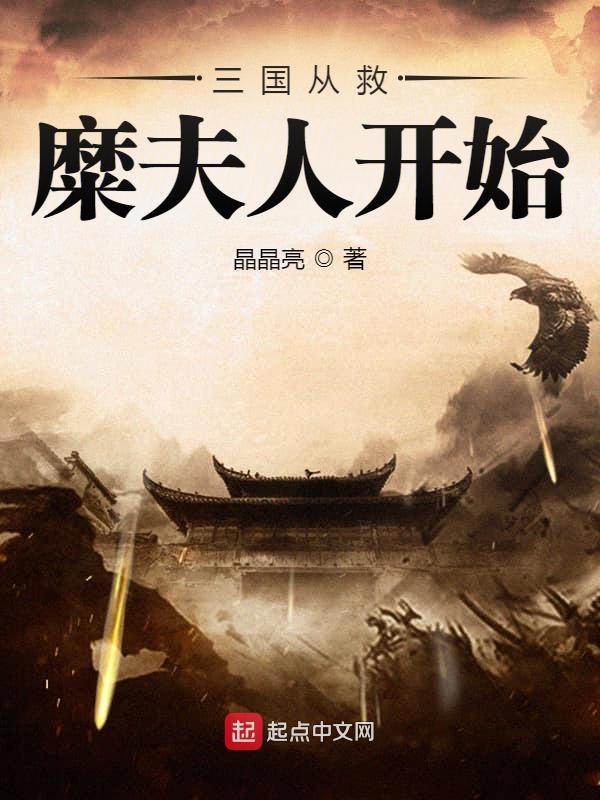笔趣啊>守陵娘子山食纪 > 5060(第19页)
5060(第19页)
“年婶子有底气,陵里的人都服她,就连陵长也听她的。”邬常安说,“你?看之前我们去抱月山换粮,胡老的话没几个人听。但年婶子不是,五年前我爹被熊咬死?了,她带队进?山找熊,跟去的都是老一辈的人,就是我爹他们那?一辈的人,他们都听她的指令。指东不打?西,让上树就都上树,没人跑。”
“真威风。”陶椿听得心驰神往,干活都有劲了,邬常安八成当不了下一任陵长,但她争取能当下一个年婶子。
挖回来的陶土用锄头和石斧砸碎,碎土过筛,草茎和石块择出来扔了,没能过筛的陶土再砸再碾再过筛。
一锤接一锤地砸土,震得山谷都在震动,夜风吹拂细土,夜空上悬挂的弯月都变得灰扑扑的。
老陶匠躺在屋里听着外面的动静,他走下床,在黑暗里熟门熟路地走到?一具简陋的木棺旁边站了好一会?儿,末了抹把眼泪,开门出去了。
紧闭的木门打?开,细微的咯吱声淹没在梆梆的砸土声中,老陶匠锁上门,他走进?人群里,说:“给我一把石斧,我也来砸土。”
“老陶匠,你?来得正好,你?来看看土筛成这样行?不行??够细了吧?”
“老陶匠,我们明?天再砍一天的树,后天烧炭,你?过来指点一下?”
老陶匠犹豫了一下,说:“我看着,不出声,你?们先自己动手烧头一窑。”
“也行?吧,不过要?是有没做好的地方你?可得说一下,烧一窑炭我们要?砍两天的树,烧毁了可糟蹋了。”
“不要?指望我,我要?是突然死?了,你?们烧炭还找谁盯着?”老陶匠笑,“烧毁了才长记性,头一窑我不出声,要?是烧毁了我再跟你?们说哪个步骤有问题。”
“老兄弟,你?还不到?五十岁,别?惦记着死?。”年婶子过来,她坐一旁说:“你?要?是嫌这儿冷清,烧完陶你?跟我们走,回陵里过冬,我给你?腾个屋住。”
“不了,我习惯住在这儿了,不喜欢人多的地儿。”老陶匠拒绝了。
“你?儿子……他是咋回事?”年婶子犹豫着问。
“不晓得,睡前还好好的,我早上喊他吃饭屋里没人应,推门进?去发现人已经凉了。”老陶匠脸上的肉又不受控制地抖动,他抬起手比划,“他半个身子歪在地上,就斜楞楞地倒栽着。我一直在想,他那?个夜里有没有喊我,应该是喊了,我没听见,一夜睡到?大天亮,早上还炒了两个好菜。”
附近干活的人停下了动作,旁的人发现他们这边不对劲,纷纷打?听怎么了。
山谷里响起一阵窃窃私语声,随即没声了,砸土的锤子落地,山谷里陷入死?一般的安静。
老陶匠接过一个石锤砸土,熟能生?巧的动作、熟悉的敲击声和浮土味,让他缓和了情绪。
“年芙蕖,托你?个事,我死?了之后,你?让我跟我儿子合葬。”老陶匠说。
“行?,你?的丧事我操持,我要?是死?了,我让我儿子来操持。”年婶子一口答应,“你?儿子埋在哪儿?”
“以后你?会?知道。”老陶匠不答。
年婶子不好再问,她拿过一个竹筛筛土,让自己忙活起来。
“你?还能看见他儿子吗?”邬常安凑在陶椿旁边小声问,“你?帮老陶匠问问,他是咋死?的。”
陶椿给他一拳,“没看见,别?乱说话。”
“噢。”邬常安叹一声,“可惜了。”
可惜个鬼,陶椿暗骂,他这会?儿又不怕鬼了。
忙到?月上中天,土筛完了,大伙儿回屋胡乱洗一洗,倒下就睡觉。
接下来的三天如第一天一样,白天上山挖土,夜里砸土
筛土。
年婶子说到?做到?,这三天她一直盯着李大爷老两口,老两口没法偷懒,累得像老骡子一样拉着脸,怨气深得见谁都没有好脸色,尤其看陶椿不顺眼。其实他们也恨告状的花红,不过花红有年芙蕖当靠山,他们恨也是白瞎,只能把怨气加注在陶椿身上。两人一致认为要?不是她挑事,年芙蕖压根不会?找事,跟往年一样,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。
第一窑炭烧成了,陶椿听说这窑炭烧得很不错,吃过饭她跟邬常安一起上山去看。
“呸,离不了男人。”李大娘大声骂。
陶椿回头,她可烦死?这个老太婆了,她挖土的时候撅个屁股她要?唾一声,休息的时候扭个腰劈下腿她也要?呸一声,邬常安给她捏胳膊提水的时候,她更是眼睛要?翻到?天上去。
“你?在说我?”陶椿退回去问。
李大娘偏过头不理她。
“不敢承认?也就这点本事。”陶椿哼一声,她抱臂得意地说:“对,我离不了男人,那?又怎么样?我有男人伺候我高兴,我舒坦。他就乐意给我开小灶做饭吃,他就喜欢给我烧洗脚水,他还要?给我洗头呢,我没肯,就怕你?眼馋。”
其他人哄笑出声。
“还有要?说的吗?”陶椿歪头问。
“不要?脸。”李大娘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