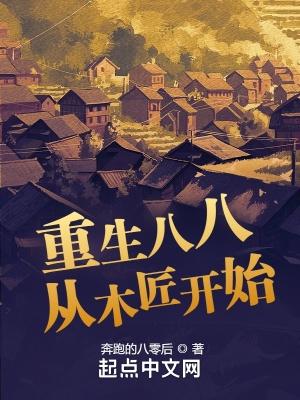笔趣啊>我娘四嫁 > 6070(第31页)
6070(第31页)
“真是神了……”越群山呢喃着,道,“那云渺,下回能否再去请这位画师做一幅画?钱只管拿,你将我的容貌也告诉他,叫他为我和你娘共同做一幅画!”
“呃……”
越群山兴致勃勃,满是期待。
祁云渺到底不好叫他难堪,而且想那画师,应当也是可以同时将两人入画的,便点点头,答应了下来。
“那我过几日去问问。”
“好!”
越群山捧着沈若竹的画像,将画像与沈若竹本人仔细比对着,一边不断感叹着传神,一边已经开始期待起自己与沈若竹一同入画的模样。
祁云渺见着他的样子,眯起眼,仔细回想了下自己当初刚见到越群山时的模样。
那时他在她心目中,还是威风凛凛的大将军,身材威武,号令三军,肃穆威严。
哪里是如今这般笑起来一点儿也不值钱的模样。
她也不知道,到底是对外肃穆威严总是板着脸的越群山是真正的越群山,还是在她阿娘面前,时不时便乐得同个稚子般的越群山,才是真正的越群山。
沈若竹的画像是拿回来了,但是到最后,对这画卷爱不释手的人,却并非沈若竹自己,而是越群山。
这是祁云渺万万没有料到的事情。
不过也好,越群山专心欣赏着画作,祁云渺便有功夫拉着阿娘到边上,悄悄道:“阿娘,我有事情想要问你。”
“你说。”
沈若竹见祁云渺这般神神秘秘的,特地躲着越群山将她给拉到了院子里,便也同样放低了声音,和她道。
“阿娘,我想问问你阿兄和相爷之间的事情。”祁云渺紧接着便道。
“裴荀和裴则?”沈若竹不解。
“嗯。”祁云渺点点头。
上午在相府里发生的事情,裴则用来掩饰心思的手法,如斯拙劣,她可不会轻易便真的被他给糊弄了过去。
不过裴则不愿意讲,祁云渺也不逼他。
她记得,当初她和阿娘还在相府时,阿娘便同她说过,阿兄和相爷之间有隔阂,并非是一朝一夕了,她若是感兴趣,可以试着帮帮他们,若是不感兴趣,便不必
掺和了。
祁云渺从前在相府,没有兴趣;
但是今日她再见到这对父子,她觉得,自己或许应该帮帮他们。
阿兄和相爷都是好人,几年不见,他们之间的隔阂好似越来越深了,他们到底是父子,有什么是能叫一对父子彼此冷漠成这样的呢?
沈若竹听罢祁云渺的缘由,恍然大悟。
但是她回头,看了看屋中的越群山,并没有选择立刻便在院子里告诉她真相。
她叫她先回去自己的屋中,晚上她会去找她,到时候再把他们父子之间完整的故事告诉她。
祁云渺便回了自己的院子,专心只等着阿娘晚上过来找自己。
在外头跑了一上午,祁云渺回到自己的院中,还得练武。
因着自从十岁起,她便几乎每日都要习武,一练就是好几个时辰,所以祁云渺在自己十岁那年开始,便有了每日沐浴的习惯。
晚上沈若竹来找她的时候,她正用木槿叶和桃枝煎出来的水洗了头发,浸润着桂花香油的乌发在幽夜中泛着黑亮的光泽,还飘着淡淡香气。
沈若竹手中握了一阵灯,走到祁云渺的床边坐下,嗅着淡淡香气,这才终于和她讲起裴荀和裴则的过往。
关于这对父子的事情,沈若竹大部分都是在当初进入裴府之前得知的。
她告诉祁云渺,裴则之所以一直和裴荀不睦,归根结底,是当年裴则的母亲过世时,裴荀并不曾陪伴在身边,甚至是过了快一整日,他才赶回到的家中。
年轻时候的裴荀,将官场看得无比重要,年纪轻轻三十出头便坐到了知枢密院事,掌管着大半个枢密院军务,位同副相。
裴则的母亲柳氏过世的那一年,正是他升任知枢密院事的第一年,是以,他很是忙碌。
因为忙碌,他没能赶的上自己发妻的最后一面;
因为忙碌,他在自己发妻丧事时,还屡屡因公务奔忙,无法全心全意地安排事情。